走不出故乡,或许是走不出自己心的皈依。
一
走了半生的路,却始终没能走出故乡的土地。
故乡是什么?故乡是黄昏的老屋,风雨飘摇而温馨永存;故乡是门前的老槐,枝叶飘零却生命旺盛;故乡是潺湲的小河,默默无语但川流不息;故乡是散发着青草香味的泥土,变迁不尽可气息氤氲。同样的意思,我在另外一篇散文中做过同样的表述,只是,那时说的是祖籍。
祖籍而故乡,故乡而祖籍,无非就是那片曾经生活过的土地。
做梦时,永远是在故乡。梦中的自己,没有年龄,也没有身体,只是一个概念,一个和谁一起做事、说话,或愉悦,或惊恐,或紧张,或舒心的存在。梦中的故乡永远是几十年前的老样子。石头铺就的街道,石头砌垒的院墙,石头碾子,石头磨盘,石头窑洞。河里滚动着卵石,地边堆放着碎石……这是石头的世界,石头的天地。
坚硬是故乡的精神,故乡的特质,但松软温馨的泥土,却是她的本质,一如母亲的怀抱。
一脚踏上她松软而温馨的土地,就有一种踏实的感觉从脚下升腾。
终于回来了!
但这里的一切已不同于梦中,一切都变了样。
沿着石砌的小街,行走在湿漉漉的雨中,没有雨伞遮护,一任细雨打湿你的脸,你的头,你的肩,你的上衣,你的脚。小街很短,走不了多久便到了头。伫立在雨中,想寻找童年的影子,可眼前的景色,与心中的记忆,使你产生疑问,这是我走了半世的故乡吗?

侯讵望。
一张红扑扑的脸从谁家门后闪出,粉红的衣衫,漂亮的蝴蝶结,张望着雨中的人影。回头去,却是一扇紧闭的大门,门上斑驳的对联依稀是数十年前的遗痕。小姑娘去了哪里?她是我曾经心仪的美人吗?她好吗?她嫁到了哪里?嫁给了谁?那人待她好吗?
我永远不会知道,因为我不会去破坏这已经平静的心绪,不会毁坏这心中雕塑的神圣,也不会改变这已经宁静的平衡。
我知道,时间的脚步碾碎了许多人的许多甜梦,我的梦无非是这无数梦中的一个而已,别无其他深意。梦的种子,会在现实的时空中开出无名的小花,一如这惆怅中立在深秋的野花,顶着风雨,鲜艳而寂寥地盛开。
牛羊的叫声早已远去,没有鸡鸣,也没有狗吠,放牛人的鞭声呢?谁在喊孩子回家吃饭吧,那么急迫,那么生硬,谁呢?母亲吗?细听却没有声音,只有雨声越来越急,越来越大。
故乡就是这样一个地方:是每一位游子心中的牵挂,心中的圣地,心中的殿堂。故乡是心中温习一遍又一遍的功课,读她千遍万遍都不觉厌烦,见她千次万次都看不够,抚摸她千回万回都亲切如初。
这就是故乡。
二
躺在村庄对面的山坡上,嗅着雨后泥土中散发出的清香,这是城里多少年未曾感受过的气息,温馨而亲切,舒爽而欣悦。故乡的气息,只有与她生活过的人才能辨别出来。草欣欣然,庄稼欣欣然,树木欣欣然,飞过头顶的鸟们欣欣然,一切皆欣欣然。这与自己的心情有关。当我们高兴的时候,甚至连狂吠的野狗的叫声,听来都是悦耳的欢呼。我们常常被自己的心情左右着而不自知,以为是外面的境界左右着我们的心情,其实恰恰相反。
快乐是我回到了故乡,快乐是我可以再次亲近这里的土地,快乐是我知道我的故乡还是过去的故乡——虽然她显得苍老而陌生。
多少年来,我们与脚下的土地在走远。
我们好久没有这样呼吸过青草的气息,牛粪的气息,庄稼的气息,泥土的气息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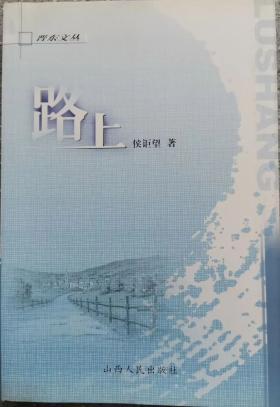
今天,对,就是今天,你回来了,土地在你身上烙印的记忆重新接上了密码,她说:是的,是的,你就是这片土地的儿子,你从这里出生,你或许将来还要回到这里。你有了一种异样的情愫,有了一种叶落归根的感觉,有了一种脚踏实地的沉静和安详。你感动,感动得热泪盈眶,泪眼婆娑。
故乡的气息就是这样。
青草的味道,是那种很好闻的味道,除了在山坡上,也在饲养棚里。那里成抱成抱的青草,切碎了,喂给那些出力的马呀,牛呀,驴呀,它们熟悉这味道,它们是这味道的鉴别者,它们打着响鼻说:对了,就是这样。
三
老槐树见证了这里的一切,年长者的离世,幼小者的成长,游子的回归,打工者的远走他乡。在这株老槐面前,一切都是秘密,一切又都不是秘密。
故乡的秘密在村民的记忆里,在老爷爷代代相传的故事里,在老奶奶一遍又一遍的童谣里,在小伙子相互调侃的玩笑里,在大姑娘回眸一笑的眼神里。
然而,故乡真的有秘密吗?我开始怀疑,后来是肯定,再后来,我也有些迷茫了。有些东西,或许就是秘密,或许只有这块土地的人才明白,或许走出这道山沟,别人就不知道你在讲什么,做什么,想怎样了。
村街的夜是清凉的,微风轻拂将夜的味道送过来,那是怎样的气息呢?舒爽而新鲜。乘凉的人们端着海碗走出家门,那多是成年的男人,还有我们这些不更世事的小人儿,我们在默默地吃饭,默默地倾听,或在街上东边西边疯跑,反正,夜是我们的,是属于这个宁静安详的小山村的。
这是生长故事的土地,这些故事就是这里的秘密。
民间故事的起因有好多种原因,反正,一个话题被提起了,便引出了别人的故事。比如,刘秀“走国”吧——刘秀与这个小小的山村有何关系呢?似乎八竿子打不着吧?有人会告诉你,其实,刘秀来过这里。话说当年,刘秀下凡,从天上来到人间,与二十八宿约定好,要到人间拯救衰败的西汉政权,到了人间,约好保驾的大臣却分布在各地,刘秀要靠两只脚走路,寻找回这些失散的大臣,以便起事夺取政权呀。这样就走到了我们这里。
别人会问,何以证明呢?
那人会慢慢悠悠回答,隔山那边的川干,其实不叫川干,而叫“酸泔”。当年刘秀走到那里,时近中午,又渴又干,走进一户人家,说:老人家,给口水喝。老人犹豫了半天,说,先生,我们这里缺水,想喝水却是没有,有沤酸菜的菜汤,客人将就喝两口吧。刘秀接了老人的酸菜汤一喝,差点把牙酸掉。抹抹嘴,叹口气说:唉,好穷的“酸泔”呀!于是,川干就这样叫出来了。
有人不服气:你见来?
那人依然不紧不慢:只有古来话,谁见过古来人。
话题从此转到是否有古来人的神话上。
有人说——说话的是位老者:早年间,张家庄有个谁?“谁”是我说的,老人当时说的是张某某——有一年冬天往川干送炭。路过一家门口,他告一块儿赶脚的同道说,上一世,他就生活在这家人家,死后,投胎转生到了张家庄。说完这话时间不长,他就肚子疼得走不了路啦,他赶紧拜菩萨,忏悔自己的罪过,过了一阵才好。从此,他再不敢乱说。到底他是胡说,还是真有转生这回事,谁知道呢!
可不真有啊!另一个说:也是张家庄人,从小没念过一天学,也没离开村子出外跑过买卖,也没人教过他,居然能讲整本的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》。
在这样的文学启蒙环境下,想不着迷文学也难。文学的根就是在这样的夜幕中开始发芽,最后逐步生长起来的。如果说今天自己能够写一点让人还稍微感点兴趣的文字,是这片神秘的土地遗传的基因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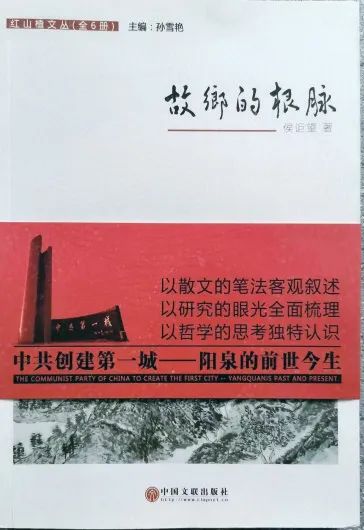
故乡迷人的夏夜,就在故事里进入梦乡。其实故事不独生长在夏夜,冬夜微弱的油灯下,同样适宜故事的生长。漫长的冬夜,四周一片静寂,连狗的叫声都听不到,雪落在房上,草垛上,门洞里,井台上,窸窸窣窣,透过玻璃窗冻结的冰花,一亮一亮的雪片斜斜飘下来,美丽如童话。一家人围坐在热炕上,油灯的灯花一爆一爆跳跃着,欢快而温馨。不是为了说话,不是为了叨咕,手里剥着玉米粒,为给不善熬夜的小辈们一点精神,长辈便开始说故事。那依然是生长在这片土地的故事,比如藏山大王的故事,比如仇犹国君的故事。都是与脚下的大地有关的生存密码。
真的,故乡真的有好多民间故事,北面有“碧屏山”,又叫陆师嶂的,那里有六位得道高僧从山中的六师洞中消逝了,至今不知所终;东面川干的故事就不说了;西面张家庄也充满了故事,南面的禁山里,也有说不完的故事。只是,这个小小的山村,却如谜一样,哪年立村,谁人所建,其来多久,没有谁能为我讲清楚。
我徘徊在短短的村街上,望天空飞落的流星,童年的记忆就这样复活起来,似乎满街都是喧嚣,满街都是热闹,满街都是生气。
四
前两年,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,《柏泉不仅仅是泉》,文中对自己的家乡做过一些记述。柏泉过去称“百泉”,因水泉多故。明版《盂县志》上说:“六祖师辿”“在县北四十里百泉山”。可见,那时的柏泉其实就是“百泉”。柏泉是由三个自然村组成的村庄,分别是红崖底、张家庄、田家庄,当地人也有以“三柏泉”称呼的。清朝的时候,三个村为一个村,对外就叫“柏泉”。新中国成立后,分成了三个行政村。其实三个村同处在一道山沟里,就叫柏泉沟。从苌池镇向北往藏山去,只数东边的山沟,第一道大沟应该是东掌沟,那是苌池村的地界,再往北,另一道向东的深沟,就是柏泉沟,再下去就是藏山沟了。
柏泉也有一处有名的风景,就是“碧屏山”,也称陆师嶂或“六师嶂”。明万历四十八年的一通古碑《柏泉村神山禁谕碑记》上说:“县北离城四十里,古刹玉帝庙有六师辿”。关于陆师嶂的传说小时候就听长辈们讲过。我爷爷告诉我,从前,那里住着六位僧人,后来,他们走进陆师嶂的一个山洞里,洞很深,里面能听到平山人簸黑枣的声音。后来,这六位就再没有出来,传说是成仙了。乾隆版《重修盂县志》的记载是:“六师嶂,山名,传上世道士六人尸解处。一名碧屏,高逼霄汉。邑王珻记略云,嶂出众山之上,崖削如屏,游客名碧屏山,而土人仍谓之六师嶂。传有六羽士化于山之洞。洞极邃,束燎入,或二三里不能穷,多燎灭而反。有庙构于嶂之腰,门繇裂石入,庙后倚深岩,池水幽暗,深不可测。”看来,成仙的是道人而非和尚。
王珻先生是盂县清初著名的人物,曾登第康熙丙戌进士,后改庶常、翰林院检讨,做过十数年的晋阳书院山长。明代邑人张拳曾有《六师洞》诗一首:参破元机控玉鬃/三茅隐映碧萝重//松巢鹤去烟霞满/丹照人稀蔓草封//花谢石男缘雨瘦/臼残云母任泉舂//仙师去后无消息/万古青青数点峰。盂县著名文人武全文先生在他《仇犹山水记》中,把碧屏山、李宾山和温泉峡列为当时盂县山水的前三名,谓之“三甲”,藏山不在其列。现在藏山之名,早已远远超越了碧屏山,成了盂县甚至阳泉市的重要名胜,而近在咫尺的碧屏山,却仍然没有开发,处在一片荒凉之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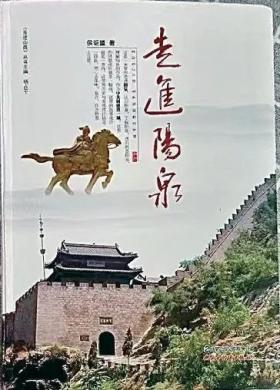
我在很小的时候,大约六七岁吧,曾经于阴历四月十五藏山赶庙会的时候,路过那里,与同行的叔叔、哥哥们做过一次游览。甚至找到了道士羽化的山洞,点着打火机进去了一节。倒也没有见到什么奇特的景致,只是洞里淤积了许多泥土,使本来不是很高大宽泛的石洞逾亦憋窄。
准确说吧,我的真正的出生之地在田家庄。田家庄没有一个姓田的人家,我后来考证,应该是城里田家的庄户地。田家者,最有可能的是盂县北庄村的田嵩年。田嵩年,字季高,盂县北关人,嘉庆二十五年进士,历任庶常、翰林院编修。他家有庄子地在我们村,也就不是什么稀奇事。但对盂县民俗颇有研究的我的弟弟,对此却另有一番说词:“田家庄不可能是田嵩年的庄子。侯家最初到田家庄种户地的侯运泰老祖是清康熙中人,《重建藏山捲亭记》碑立于康熙五十一年,侯运泰是苌池村纠首,家谱上运泰和碑刻上运太应为同一人。据传刘家比侯家早到的田家庄,而史家应该还在刘家之前,也就是说他们大概清朝以前就到田家庄居住了。张家庄的俊娃老人50年前就说过,侯家搬过来差不多300年了。所以田家庄不可能是清嘉庆时的庄子。”也许,他是对的吧,我也不想去管它了。
但这样的历史积淀,这样的文化传承,这样的古迹名胜,对于开始做梦的山里娃,那一定是一种慰藉、一种熏陶、一种滋养。
五
也许,我的文学梦是从1972年那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开始的。那时我还是二年级的小学生。大约是5月份吧,天气还不算太热。我站在学校院子的正中偏南,望着阳光从东边教室的屋顶,射向西边老师办公室兼宿舍的窗台,齐齐地在窗台上划出一条线。
在那个时间段,我居然闪出一个奇怪的念头,我想留住这一刻的时间。希望在若干年之后,我还能记起那时的状态:学校、教室、老师、同学,以及教室外墙上的标语和南边教室门口刚刚盛开的粉色芍药花。也奇怪,几十年过去了,那一刻的情景居然被我记住了,而且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显得模糊起来。
那是故乡的一个特定场景。我想之所以难以忘记它,大概是因为故乡是我们每个人记忆深处最清晰的画面和旋律,是我们开始做梦的地方,是自己人生的出发地,更是我们每个人的根脉所系。
我的小学是在一所神房院里。神房不同于庙宇、寺院,是供神圣临时歇脚的地方。准确说,是藏山大王歇脚的地方。藏山大王就是赵氏孤儿赵武。我们当地有藏山大王崇拜。遇到旱灾年景,邻近村庄都要赴藏山庙祈雨。即便是好的年成,也是他老人家保佑的结果,每年要确定一个村庄做会,就是请他老人家到村里巡游,人民通过表演社火把戏,讨他老人家欢心。
学校为复式教育,算术、语文、政治之外,诸如体育、音乐、绘画都有课程安排。遇到节日,还要排练文艺节目,比如秧歌剧什么的。我自己曾参演过一出秧歌剧《老两口争扁担》。我在剧中饰演老汉。记得有两句唱词:星星忽闪天未明,老汉我早早起了身……说的是老两口为了抗旱保苗,早早起床,争扁担挑水浇地。老汉以为自己起得早,结果老伴比他还早,两人争执不下,由队长来评理矛盾才得以解决。这个剧带有当时的时代特征,但每次演出,老百姓都兴致很高,得到夸奖的滋味总是很甜美的。
那时我不但演剧,而且说快板,说评说(我们当地的一种曲艺形式)。文艺的实践,使自己萌生了写剧本,编快板、评说段子的念头。这或许就是文学梦开始的时候。
这么说吧,从小学开始,到初中、高中,再到中专,一路走来,自己都是文艺队伍中的一员。骨干说不上,但也偶有上佳表现。同时,在各个学习阶段,在老师安排下,办板报,写通讯稿都无形锻炼了自己。
直到后来背着老师和家人偷偷开始写小说。那时投稿不用贴邮票,信封剪个角,让邮递员寄出去,投稿就完成了。每次投稿之后,接下来就是等待。在焦急等待中,做着各种美妙的猜想和期盼。当然,结果可想而知。一开始只有退稿和铅印的退稿条,后来,偶尔也能接到一份编辑钢笔书写的退稿信。那时晚上做梦大都与投稿有关,不是梦到稿子丢了,就是梦到作品发表了。醒来,望着黑黢黢的窗户,心中空空荡荡。枕边却有梦中落下的泪水。
如今已过花甲,这文学之梦依然没有醒来。每天不写点东西,就感到空落落的,似乎生活缺少了点什么。后来,我想,这也是一种爱好。就和有的人喜欢唱歌跳舞,有的人喜欢旅游摄影,也没有什么不好。既然是爱好,就让他爱下去得了。总结这几十年,我也有这么个感悟:也就是人一定要有一种乃至几种好的爱好,这样生活才充实,才有意义;而爱好,又是一个人成功的原动力,只有打心底里喜欢,才有继续坚持下去的勇气和韧劲。
当每天新的阳光洒满窗台的时候,我依然会记起我的故乡,以及与故乡有关的山山水水、事事物物、男男女女,想起自己曾经开始做梦的地方,想起自己曾经做过的梦。
作家史铁生说过:皈依在路上。我们躁动的心,只有在故乡的土地上才能找到安宁,否则永远在路上。其实,把心安放在故乡的土地,何尝不是另一种皈依,但其实,也还在路上——因为,故乡也在前行。所以,故乡便成为一种记忆,一种憧憬,一种奢望,一种心结。
走不出故乡,一如走不出自己的心结,无论我们走千里万里,无论我们走十年八年,故乡永远驻足在我们心里。
走不出故乡,或许是走不出自己心的皈依。
作者:侯讵望
名家简介
侯讵望,1963年7月生,山西省盂县人,现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,曾任山西阳泉市文联、作协主席。出版有杂文随笔集《学会忍耐》,中短篇小说集《致命诱惑》,散文集《路上》《我是谁》《走进阳泉》《故乡的根脉》《心中的雪》等,电影剧本《伏击》(合作)、《中共第一城》等。作品曾获中国小说学会“中国当代小说”奖,《小说选刊》首届全国小说笔会征文短篇小说一等奖、中国散文年会“十佳散文奖”、山西省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赵树理文学奖、山西省文艺评论奖等。










